乐都小城生活记录
一九七零年仲夏时节,当我第一次乘火车从兰州爬上青藏高原,我曾痴痴地一直扒在车窗前向外张望,试图将高原的苍凉与壮观全部印记在心里。
蒸汽机车沉重地喘息着,拖着一列长长的深绿色车厢,在车轮与铁轨“咯噔”“咯噔”的撞击声中缓慢行驶。随列车西进,人烟越来越稀少,植物越来越稀疏,山野越来越荒凉,到后来竟然使人觉得仿佛是在毫无生气的火星上旅行了。太阳照射着湟水粼粼闪烁的河面;那深陷在河谷中的银色水流,弯弯曲曲,随逐渐抬升的地势上溯到遥远的西部天际。
三个小时之后,列车驶入一个小盆地,停靠在一个叫做“乐都”的小站上。旅客眼前一亮,窗外出现了郁郁葱葱的杨树林和硕果累累的果园,山坡与河岸上开遍鲜花,田野中种植着马铃薯、春小麦、蚕豆和油菜,盛开的油菜花就像黄金铺成的地毯;平屋顶的农舍分布在水渠边,掩映在玫瑰和丁香树丛之中。在火车上可以看见乐都县城的半条街,两三层高的楼房鳞次栉比,行人如织,让人对在如此偏僻的荒山野岭中居然还有这样一块人类的聚居地而感惊讶不已。
乐都小城位于来自西部的湟水河与从北部群山流下的一条叫做“引胜沟”的川水的交汇部位。沿湟水河谷西行六十千米,就是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乐都县城的主要部分在河谷的北岸;沿川水“引胜沟”北行九千米,有一个小山村叫做熊家湾;后来我的同事们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地震台。我曾在那座台站度过许多快乐的日子。在河谷南岸的山地中,距县城二十千米,有一座著名古刹,叫作瞿昙寺;我和朋友们曾露宿在它的大门外,在那里实施地震野外监测。这两处地方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实际上,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每年秋天,我都会去乐都县参加省科委组织的支农义务劳动。我和来自盐湖研究所、高原生物研究所和青海计量所的同事们一起,在乐都的田野里帮助农民抢收小麦。那时没有收割机,我们象虾一样弯着腰,用镰刀将麦子齐根割倒,用麦秸捆成一束束,再集中起来,让麦穗朝下,堆成一个个麦垛。休息时,大家靠在田间地头的麦垛上唱歌;其中有一首美妙的俄罗斯歌曲令我难以忘怀,歌中唱道:
“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云雾在荡漾;
微风轻轻吹来,
掀起一片麦浪。
……”
到了晚上,我们四仰八叉地躺在谷仓里的麦秸上,倾听高原风暴的呼啸和淅淅沥沥的雨声。
那歌声、那风声、那雨声,至今仍常常回响在我回忆西部的梦境中。
一九八四年八月末,青海省东部地区发生一系列小地震,虽然震级不高,但西宁和东部地区震感明显,造成普遍的恐慌。那时,对于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惊天惨剧,人们还记忆犹新。
我们的地震分析预报研究人员相信,这些小地震很可能是一场破坏性大地震的前兆。为了加强地震监测,青海省地震局决定在乐都县城南部增设一个临时地震观测站,以便配合西宁地震台,确定这些“前震”的震中位置。临时地震观测站的位置被指定在瞿昙寺。
于是在九月上旬一个晴朗的早晨,由老孔局长亲自带队,我同四位朋友一起,乘北京吉普,押着一辆载重两吨半的卡车,载着一台单分向地震仪、必需的消耗器材和两顶单帐篷,迎着高原秋天的太阳上了路。
汽车沿着陡峭的湟水河岸,在“搓板路”上狂奔三小时,到达乐都县;然后折向南,过了湟水大桥,经过一大片刚刚收割过的麦田,进入到群山当中。这里的山野十分荒凉,极目望去,所有的山坡都是光秃秃的,裸露着夹带石膏层的铁红色泥页岩;只有在幽暗的峡谷里才零零星星生长着几丛矮小的灌木。
在山地中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又剧烈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到下午两点,眼前出现一块开阔地。我们在路两边看见成排的老榆树和老柳树、懒洋洋地啃着路边青草的耕牛、还有丁香丛围起来的低矮农舍。接着,在我们的右侧,出现了一片宏大而破旧的寺院。这就是瞿昙寺。
我们全身的骨头几乎被颠散了架,同时担心那些脆弱的仪器设备是否已经散了架。我们在瞿昙寺前面的石阶坐下休息。那地方的村支书,一位穿着肮脏的黑衣服、胡子巴茬、灰头土脸的中年男子跑了过来,说他已经接到了公社的通知,由他们村负责接待“省上来的地震专家”。
不一会儿,两个村民小心翼翼地推着一辆架子车过来,车上装着碗碟和筷勺,一只盛了开水的大铁桶,一只盛满甘蓝炒羊肉的大搪瓷盆和两个装满馒头的柳条筐。当考察队员们享用午餐时,村支书和那两个村民就蹲在一边,掏出烟丝和裁好的旧报纸,抽起烟来。
老孔局长一边进餐,一边向村支书讲解“当前地震形势”;那村支书似乎不大相信这里会有破坏性地震发生,说从他爷爷的爷爷开始,他家连续好几代人就住在这里,一直都是很安全的,从来没遇到过大地震。
“唐山人一九七六年以前也没有遇到过大地震。”老孔局长道。
“你们不是来制造地震的吧?”那村支书直愣着眼珠,小声问道。“要是这样,你们可不要毁坏了我们的房子。”
老孔局长告诉他不必害怕,事情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这一行人是来用仪器记录天然地震的。他进一步解释说,通过对小地震的监测,可以判断今后会不会发生破坏性大地震。
“好,好,那就好,那就好!”村支书放下心来。
“我已经带来省政府的介绍信。”老孔局长说,“不止是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下一步拾振器选址的工作也要你们配合哩。”
“啥?”
“就是让你们帮助找一块地方,安装测量地震的仪器。”我解释道。
“莫温词(青海话:没问题)。”那村支书答道。
为了寻找一块安装拾震器的基岩露头,我们随村支书围绕瞿昙寺那座古刹转了两大圈,又在寺庙大院里转了个够。
瞿昙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宗教建筑群,占地约四公顷,总建筑面积差不多有一万平方米,始建于十四世纪末明王朝建立初期,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在随后的三百年间,这座寺院一直香火缭绕,僧众如云;但到了清代,有一个时期因为据说有反政府倾向而遭遇关闭;但其真正的衰落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在经历了三十多年革命的疾风骤雨的冲击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瞿昙寺已经被彻底摧毁。
当时瞿昙寺破败的惨状,曾令我和我的朋友们唏嘘不已。
昔日诵经念佛的僧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佛像倒塌,法具损毁。几处庙堂只剩下了一堆堆碎砖烂瓦;其它的殿堂也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粗大厚重的圆木廊柱东倒西歪,上面的油漆早已剥落,精工雕凿的门窗半悬在那里,随时都有跌落的危险;亭台只剩下几根开裂了的木柱。门前台阶的石板被撬开,有些已然被搬走派了别的用场。屋顶长着一缕缕茅草,迎着秋风摆动。只有一处大殿还算完整,现今成了公社的仓库,窗子紧闭,朱红色的大门上挂着生了锈的铁锁。由断壁残垣围起来的院子长满荒草,石板路也被从石缝中钻出来的车前子和蒲公英遮蔽了。寺院周围的一些老柳树和老榆树,枝杈都被农民砍去作了柴火,只剩下了活树桩。
由于在瞿昙寺附近实在找不到完整坚硬的基岩露头,我们只好把拾振器安放在寺庙前一顶倾废了的凉亭下面作为基座的砂岩上。据村支书讲,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基岩。无人知道它究竟是一块孤石还是地下完整岩体的露头,不过我更相信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我们真正需要的基岩。记录器安装在庙门口,架设在从小学校搬来的一张摇摇欲坠的破旧课桌上。
然而命中注定,这是一次失败的野外考察。
一切准备停当。傍晚,观测开始。接通直流电源后,记录笔在铜板纸上画出兰色的线条,每当石英钟秒针越过“12”时,笔尖轻轻一抖,画出一个清晰的尖脉冲。大家都舒了口气,庆幸仪器没有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颠簸中遭到损坏。
然而我们高兴得还是太早,仅仅过了二十分钟,仪器就开始犯病。记录笔就跟中了邪似的,先是高频震荡了一阵,然后就扭头靠在一侧,执拗地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却又发疯般地在记录纸上乱画起来。突然“啪”的一响,什么东西从机箱里飞了出去,让我们吃了一惊;再看那记录笔,早已不知去向。
我们都知道这种国产的专门用于野外考查的地震仪不好伺候,它的电子放大器是最调皮捣蛋的部件,一到节骨眼上就容易掉链子。每次出发前在西宁的仪器室调试的时候都好好的,可是一旦到野外派上用场,那些该死的器件就出了问题。这次也是一样,又是电子系统发生故障,任凭我们的电子专家怎么鼓捣,还是完全不能正常工作。
“怎么啦,同志们!又吃苍蝇了么?”老孔局长急切地问道。
大家沉默不语,只有仪器组组长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耸耸肩,沮丧地回答道:“又不灵啦!”
“又是这样!”老孔局长生了气,“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哎呀,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我说你们什么才好哇。”
他朝在场的每个人环视一遍。“裘的,你们都傻站着干什么呀?倒是赶快动手修理啊!”
“修理……要用到……电烙铁,”组长说,“电烙铁……需要用二百二十伏交流电。可是在这儿,到哪儿去找交流电啊?……也许,我们该带一台罗宾(ROBIN)发电机来的。”
老局长脸色铁青,鼻子都气歪了……
大家风餐露宿,在瞿昙寺坚守观测岗位。白天,当仪器工作状态比较平稳时,我们也会轮流到寺庙里去参观。我们惊动了栖息在那里的无数乌鸦和老鼠,在荒草萋萋的庭院和散发着霉朽气味的殿堂里面转悠,观赏残破廊宇上那些模糊的壁画。到了夜晚,我们就卷缩在帐篷里,听山风吹过古庙时发出的呜咽声,或者点上蜡烛,玩一种叫做“四十分下台”的扑克牌游戏。
这次野外观测进行了半个月;中间更换了几台仪器,经过十几次修理,虽然记录断断续续,倒也记到几个1.0级左右的小地震。可是这样的资料,对于地震预报研究来说实在是毫无价值。让老孔局长承认失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最终他还是同意撤回西宁,在一个阴雨天里提前结束了这次考察。
分析预报人员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他们一向蔑视的“土八路,地方军”——乐都地震台。根据这个群测群防性质的地方台站的记录,这段时间里,在半径五十千米的范围内的确发生了几十次小地震。那个被认为是大地震前兆的小震群,似乎并没有持续太久。要确定它们究竟是不是一次大地震的前兆虽然并不容易,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预报人员当初的推测是完全错误的。
青海省地震局一直希望在西宁东部建立一个正规的地震台,加强地震监测和前兆研究。这个愿望并未得到国家地震局的支持,但却得到乐都县科委的积极响应。县科委已经成立了地震工作办公室,期望能有一个真正的地震科研实体。于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省政府的慷慨资助下,一个地方台站——乐都地震台应运而生。
省地震局群测群防科的工程师马京生先生和刘维宪科长,是这项工程的积极推动者。经过技术人员的实地测试考察,他们最终将台址选定在县城以北九千米的熊家湾。那是川水“引胜沟”西岸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
引胜沟,是一条山谷,或者不如说是一道长长的河漫滩。平日里,它只是一条在鹅卵石当中潺潺流淌的小溪,既清澈又温柔;只有在下雨之后的几天里才会成为一条真正的河流。实际上,引胜沟就是北部群山的一条泄洪通道。这时,各路洪水咆哮着,裹挟着泥沙和砾石,在村庄东边汇合成宽阔的水面,然后,浩浩荡荡地向南方流去,涌入湟水河谷。这条河滩的东西两侧原先都覆盖着茂密的丛林,如今已经变成荒山秃岭。这条河川越往北地势越高,到了最北,地势高出将近一千米。河床在县城北端的宽度有二百米,越往北越窄,到了源头,河道就退化成一道纤细的山泉。那里云遮雾障,多雨雪,生长着高山牧草和低矮的灌木。
河滩东岸,靠近县城,有个大名鼎鼎的锻造厂,是个生产重型机械的所谓“三线工厂”,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了“备战”,从我国东部迁移过来。那工厂从迁来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没开过几天工,也没生产出几件像样的产品。虽然如此,它却顽强地存活下来。时至今日,仍有工人上班,仍有部分机床在运转,偶尔,那两个大烟囱也会冒出烟来。
而它的孪生兄弟,搬迁到引胜沟熊家湾小村附近的另一家“三线工厂”就没有前者那么幸运了。它刚刚完成厂区大门、办公室和职工宿舍的建设,还没来得及给车间封顶,当局的政策就发生了变化。工程中止,随后,那个不受欢迎的搬迁计划胎死腹中。前期到达的筹建人员回了老家,这片接近完工的建筑群就象玛雅文明一样被遗弃在荒莽之中了。工厂的废墟靠近一道灰岩山体,下面是一片年轻的杨树林。杨树林长得很快,没几年功夫就将废墟遮盖起来,使它从人们的视野中,最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马京生工程师和刘维宪科长,被县科委的工作人员带进熊家湾小村,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宝地。因为这里有基岩出露,可以满足地震仪的工作条件,没有交通和工业的干扰;附近有村庄,所以将来的工作人员不至于太孤独;水电供应方便。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有现成的房屋可以使用。
马京生工程师和刘维宪科长,是两位很精明、很会算账、也很会谈判的先生。经过一番交涉,他们只花了五千元就买下了三栋废弃的两层宿舍楼,总共一千五百平方米。此外,还免费获得一千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和库房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每平方米建筑物仅仅花了两元五角,相当于当时三斤菜子油的价钱;同时划入地震台领地的土地面积竟然有1.7公顷之多!
这两千五百平方米的建筑物保存完好,石头地基,混凝土构造柱,红色空心砖墙,预制板楼面,木门窗,电源配置齐全,可以立即投入使用。
在这个基础上,又投入了四万元,在海拔高度2170米的半山腰开辟了一个平台,修建了放置地震仪和倾斜仪的山洞、观测工作室和值班室;建造了一个五十立方米容量的蓄水池,一条通往河滩泵房的输水管道,还有一个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环境项目:台站庭院和周边八千平方米的绿化林木与花园!此外,还在河对岸一处泉水旁建造了水氡观测站。地倾斜和地下水含氡量,一直被认为是地震的可靠前兆。
乐都地震台的总设计师是马京生先生。这位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生天性开朗,知识面广,富有想象力,对这个项目倾注了全部心血,一心要把它打造成全省观测条件最好、环境最优美、最适合年轻人工作、生活的地震台站。现场工程总指挥是来自县科委的郭坚峰先生。这是个热情洋溢、事业心极强、敢作敢当、雷厉风行的人。他在施工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多次遭遇危险,最终生生地在那片荒野废墟上雕刻出一座明珠般璀璨的地震科研基地来。这两位先生后来都十分遗憾地调离了青海;如今,马京生先生已经退休,居住在东海岸一所三层的复式住宅里;在楼下一块空地上种植大葱和红薯。郭坚峰先生则跨海去了海南,成了海南省地震局的一位领导干部。刘维宪科长已经去世,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我相信,地震科研系统的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些创业者的功勋。
从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开始,我和青海省地震局的同事们就成了这里的常客。我们在这里安装调试设备,对观测仪器进行标定;作为业务教员,我也多次在这儿的教室里给全省野外台站的观测员进行业务培训和知识更新。
我非常喜欢这个处地静僻的世外桃源。
我喜欢工作之余坐在值班室的办公桌前读书。和熙的阳光从洁净的大玻璃窗射进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风儿带着花香,吹动窗帘轻舞,痒痒地抚摸我的脸颊。窗外风景秀丽,山坡上新栽的树苗已经长大,枝叶茂密,树荫浓郁;从教室通往半山腰观测室的台阶两侧,长满铁匠木和冬青类的灌木丛;花园里种植了玫瑰和丁香。春夏时节,鸟儿在屋檐上歌唱,美丽的蝴蝶漫山飞舞,花丛里蜜蜂嗡嗡。六月懒洋洋的午后,花儿的香气和蜜蜂的叫声特别能催人入睡。山洞前面的平台上,丁香树中间有一个钢筋混凝土制作的鱼池,里面放养了好多金鱼。那里还有一台反射式太阳炉,巨大的水泥抛物面反射镜将阳光聚焦在前面的一个钢架上;一壶水放在上面不一会儿功夫就开了,我们就用那水沏茶。透过林木的枝叶,可以看到比邻的熊家湾小山村,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生长着春小麦、马铃薯和胡萝卜的田地,农民的平顶屋和缭绕在村庄上的袅袅炊烟。可以望见引胜沟白晃晃的河滩、对岸灰黄色的山野。河滩和山野的景色实在太凄凉,不过这种反差却大大地增加了一个人的满足感和幸运感。这是一种生活在荒漠中的一块绿洲里的感觉,一种栖居在汪洋中一座绿岛上的感觉。
秋天的晚上,我常常会沐浴着清冷的月光,在台站通往公路的林荫小路上散步;有时也会漫步到河滩上去,坐在砾石上沉思默想,那时晚风从北方吹来,流淌的河水发出竖琴般悦耳的叮咚声。
乐都地震台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国家地震局系统的员工,但却属于地方事业编制。他们都来自乐都县城,一半是操着“嗞啊,嗞啊”的青海话的本地土著,一半是操着被称为“半炒面”、带有青海味的普通话的东部移民的子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年龄比我小十几岁。这些小弟弟小妹妹都非常可爱,阳光般的热情、山风般的清纯。他们忠厚朴实,勤奋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一丝不苟,事业心很强;而且,他们都有远大的理想,能够不懈地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当中,与我接触最多的是崔鲁辉小先生和许勤姑娘。崔鲁辉一直留在乐都县工作,后来成为那地方地震局的领导;许勤则走出大山,先是去了西宁,出任西宁地震局局长并取得高级工程师资格,后来调去珠江三角洲,进入佛山地震局领导班子。我在INTERNET上看到她给广东少年儿童讲授地震知识,回想起乐都地震台那个象小猫咪一样温顺的女孩子,似乎很难相信她们是同一个人。
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游戏,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摆脱了机关办公室的无聊与沉闷,使我非常快乐。这个大山里的地震台,因为有了我们而不再孤寂;而那个无声无息的熊家湾小山村,则因为有了地震台而变得生气盎然。村庄里的农民成了我们的常客;锻造厂的工人也经常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参观和游玩。
我最后一次去乐都,是跟杨俊峰先生和严政先生一起,在乐都地震台给全省台站人员办学习班,教授PC—1500计算机的使用和BASIC高级计算机语言编程。时值中秋佳节,那天晚上,地震台的教室灯火通明,我们吃过月饼,举行了一场中秋晚会。
每个人都有有趣的节目奉献,教室里笑声和掌声不断。
朋友们唱了许多首动听的经典民歌,有的是独唱,有的是合唱。我还记得其中那首感人至深的歌曲:
“哎!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哥象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哥啊!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哎!
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
望见月亮想起我的阿哥;
一阵清风吹上坡,吹上坡,
哥啊!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
……”
歌声就像一群白鸽飞出窗外,飞跃了山村、河滩和树林,在大西北的夜空中翱翔。那时,一轮满月当空照耀,向这个小小的地震台投下银色的月光,同时也成为青海省地震科学工作者诚实劳动和他们真挚友谊的见证。
毕剑昆 2010年4月于威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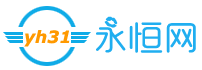

 会员登录
会员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