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爷爷一家人
回到家里,已是傍晚。兄弟三个,我回家得最早,哥哥和弟弟还在路上。过两天是母亲的六十大寿,只有这样的日子,她的三个儿子才可能从不同的省市回家相聚。
山村的夜来得格外早,晚饭毕,四处已是寂静无声,乡亲们早早地拉灯睡觉了,偶尔有几家,守着电视,却把音量调到最小。
一天前我还在繁华的京城,此时京城的夜生活还刚刚开始,满街的灯光像一条河流动着,而在雪峰山余脉的几个山包环抱的皱褶里,我生长的村庄——鹅梨坳村,正死一般的沉寂。
我记忆中的山村不是这样的。少年时村里还没有电灯,我和几位同辈兄弟要么正在煤油灯下争论着习题,或者拿腔拿调地读着课文;要么刚刚从水库里洗完澡,唱着“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想象着大海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村里没有一个人见过大海;要么就是在门口的大泡桐树下乘凉,听友爷爷讲古。那时候的村庄是喧闹的,是生气勃勃的。
父亲说,村里没有年轻人,只有一帮老人和妇女,许多细伢妹也跟着打工的父母进城了。村里没有人气了,老人们在一起闲聊时,话题就是谁的孩子打工打的好,寄回来的钱多一些。母亲说,作田不划算,养猪也不划算,每家也就养一两头猪,过年时杀了熏腊肉用。村里人平时吃肉也从集镇上买。一段日子里,哪个老倌隔三叉五,红光满面地走在村前的石板路上,扁担的一头是一胶壶的米酒,一头是一块猪肉,那么大家知道他的崽女在外面,打工打得不错。
临睡觉的时候,一个小伙子来看我,非常有教养地喊我:“哥哥”,不是母亲介绍他是堂伢子,我认不出这个曾经抱过、哄过的小弟弟。我不见他快十年了,每次匆匆回来,他要么在读书,要么在外地打工。今年他下广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回家,等着明年开春再出去。他说:“工越来越难找了,这次出去白白地送了盘费钱。”
寒暄了几句,他走了,母亲叹息说:这是个好伢崽,长得标致,人聪明,又懂事,可惜他娘死得早。
我想起了堂伢今年整整二十岁,他的出生时间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他的父亲在十里外的煤矿做合同工,家里比较殷实,他的母亲高挑白净,算是乡里的美女。他是头生子,他父亲自然欣喜若狂,打三朝那天大办宴席,晚上还请公社电影队放了两部片子,一部是《月亮湾的笑声》,一部是《花为媒》。也就是在那天晚上电影散场后不久,我爷爷去世了。因此,堂伢多大,我爷爷也就死了多少年。
堂伢一天天长大,他家是离我家最近的邻居,他的母亲立婶子与我母亲很要好。我每每放学回来后,喜欢带他玩。他长得粉雕玉琢,一张嘴甜得不得了,两三岁时就会乖巧地对我说哥哥带我去哪里哪里玩,哥哥给我摘个桃子吃等等。
后来,他的弟弟出生了,他父亲被煤矿辞了工,母亲得了肺病,家境便很快败落了。他母亲死的时候,我正念高一。暑期的一个晚上,他父亲立叔叔突然在家里大喊:“来嫂,我老婆不行了。”做赤脚医生的母亲胆子特别大,跑到立婶子床前,看到她只有出气没有吸气,知道不行了,吩咐立刻准备后事。母亲说,立婶子临死前直直地看着他的丈夫,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家都知道她在担心自己的三个孩子。那时堂伢5岁,他大弟弟梅伢3岁,小弟弟出生不到半岁,名字都没有起好,后来小弟弟送给了别人。
两年前我回家时,碰到堂伢的祖父友爷爷,我问堂伢读高几了?友爷爷说,他考高中差了2分,要多交1000元钱才能上学。家里哪有这些钱,只好让他出去打工了。
送走了堂伢,我便顺便问起了友爷爷。父亲说:友爷爷去年冬天走了,刚过完80岁的大寿。不但他走了,他的三儿子美叔叔也突然去世了。
我爷爷和友爷爷年轻时很不对付,经常吵架,但不妨碍他喜欢我,他常有些羡慕地对我父亲夸赞我:“这伢老少合三辈,会有出息,”意思是我不但和同龄孩子能打成一片,和自己的叔叔辈、爷爷辈那些成年人都相处得很好。他喜欢我大概是包括他孙子孙女在内的孩子,没有谁愿意听他讲那些没完没了的陈芝麻烂谷子,而我正相反,特别愿意缠着他讲古。讲这个村庄的来历,前面这条石板路哪年修成的,以及他上贵州做石匠遇到的种种江湖上的有趣事。他识得些字,能自己写信,手艺也不错,在他那一辈人中间,算是见多识广的。
“友爷爷有四个儿子,可死时没有一个人在身旁送终。”父亲为此感到遗憾。友爷爷死前没有一点病症和迹象,他一个人住在一间房,自己单独开火。吃过晚饭独自睡觉,第二天早晨他的一个孙女给他端洗脸水到床前,叫“爷爷”怎么也没回音,便喊来了大人,才知道友爷爷晚上永远睡过去了。——也好,这样没有痛苦地死去何尝不是种福份?
友爷爷死后不久,他的三儿子美叔叔又死了。美叔叔年轻时名如其人,是村里的美男子,文革后期各地大办高中,他从乡办的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他长于辩论,干农活时常常为点事情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一般人面对他的唇枪舌剑,只能嘟哝一句:“不就多喝几滴墨水吗?”乖乖地认输。他结婚后连续生了三个女儿,因违反计划生育家里被罚得四壁空空。他前一年在辰溪某地做工,回家不到一周就暴病而亡。有人说他是因为在湘西和人争吵,被当地的高人施乐法术,受了“神打”,然后自己浑然不知,过了一两月往往突然死亡。这些恐怖的传说使我想到了金庸小说中各种“生死符”,难道湘西大山里还有这样的种“生死符”的人?他死后,撇下了妻子和女儿,而他的二哥立叔叔丧妻多年。经人撮合后,哥哥和弟媳妇两个苦命人走到一起,两人带着各自的儿子、女儿到死去的妻子和丈夫的坟前烧了纸钱,两家便合成一家。老二家的大儿子堂伢和老三家的大闺女已经成人,他们兄妹一起出去打工,挣钱供下面的弟弟妹妹读书。
友爷爷的大儿子是一个老实巴交的退伍兵,他最自豪的经历是当年在广东某地边防部队当兵的几年,娶了个老婆是个河东狮吼,不但经常把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而且常常和村里的其他人骂架。这位婶娘似乎对“斗争”有天然的爱好,平时干农活没有精神,一碰到吵架立刻如打了针吗啡一样。她最辉煌的吵架纪录和和村里另外一个泼辣媳妇对骂,她拿一块切菜板,用一把菜刀在上面不停地砍着,在砍声的伴奏下,各种恶毒的咒语与秽语如滔滔江水,一泻而下,声音洪亮而有穿透力,一整天都不懈怠,吃饭的时候让她女儿盛一碗过来,胡乱扒了两口,又继续战斗。他家生了两个女儿,最后四处逃避计划生育工作队,第三胎终于是个男孩。现在两个女孩都在省城里打工。那个超生的儿子童年时极其调皮,经常在抗旱的时节,将人家用抽水机刚刚灌满的水田里的水全部放干。长大了又变得特别老实,跑到城里进了个烹饪学校,过年回家时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在谁家办酒席时,他去露一小手,将村里那些“土法速成”的大师傅比下去。
友爷爷生前总是两只手拢在一起,眯着一双眼,朦朦胧胧看人看事,年轻时冲州闯府的他越来越不明白这个世界。作田的越来越不想作田,村里的肥猪耕牛时不时被偷走,民风纯朴的村庄也有人出去做了“烂仔”,孩子们读书的学费越来越贵,以前的公社大队干部看到老人还客客气气可现在下乡的干部眼里越来越没有他这样的年长者。他愤怒他不解,但他有什么办法,我大学毕业后曾回家几次,和他聊天时,他总问我:“你是我们这村读书读得最好的人,你说说这世道会怎样变?”
到友爷爷死,我都未能给他一个合适的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世道会怎样变。
二、社伢的“历史悬案”
母亲大寿办酒席的那个中午,我见到了社伢。他其实是来“赶台子”的,谁家办喜事他会主动过来帮忙,比如烧火、给杀猪的打下手等等。主人看到他一人孤身潦倒,未必能让他干活,但会打发他些钱。这种以报酬的形式的乞讨使他维持一种没有乞丐身份的尊严。
看到我们兄弟,他还主动掏出纸烟来,给我们敬烟。他穿着很干净,一脸朴实的笑容,他是办“高级社”时出生的,算算年龄都四十好几了,但和我少年时的印象没有大的区别。
社伢姓黄,是和我家同一个行政村的另一村民小组的,那个村民组大部分姓张,他家是从外地搬迁来得小户小姓,再加上家境贫困,兄弟三人都在屈辱中长大。社伢一生都娶不上老婆,但大家开玩笑说他的老婆最多。因为村里的大姑娘们吵架或发誓时,赌咒的方式就是:如果我说假话,我就是社伢的老婆。或者骂对方:你这个骚货,只配嫁给社伢。
社伢名气如此之大,乃因为一件“历史悬案”,大家说他和母牛性交过。我们男孩子放学时看到社伢走过来时,一些坏小子就会大声地说:“社伢社伢没出息,只会偷偷日牛X”。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不相信这种传言,说那是因为其父他家穷,别人编排出来的谣言。但传言中各种细节却活灵活现。说一次开春犁田时,队长让他去牛栏牵头牛来干活。大家左等右等见不着他的影子,便打发一个老汉去看看。老汉一进牛栏看到他将一头母牛拴在栏杆上,自己正在后面热火朝天地干着事,牛嗷嗷地叫着。老汉大声地喊:“社伢你个短命鬼,娶不上老婆也不能搞牛婆娘呀!”
本来家徒四壁,再加上这个丑名传出去了,谁会再嫁给他?而且常常有人当面奚落他,问:“社伢,牛x的滋味怎样,亏你想得出这个泄火的办法。”社伢只能尴尬地一笑,一语不发。社伢是否真的干过那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封闭偏僻的山乡需要谈资、需要笑料。社伢当然也没有主张自己名誉权的意识,这种传说便一年年传下来了,一茬茬小孩如我们当年那洋对着他唱那段儿歌。
社伢兄弟三人,他行二。他的大哥最能干,长得高大英俊,犁田耙田、捕鱼捞虾都是老里手,是他们三兄弟唯一娶妻的人,生了两个闺女,有一年突然投河自杀了。原因是他们生产队有一夜丢了两担新收进仓库的稻谷,队长便带人一家家搜查,在他家看到有和陈谷颜色不一样的新谷子,便断定他是偷谷的贼,而且他家穷,符合做贼的推断。但他死活不承认,于是队长和大队干部对他实行专政,晚上将他绑了起来,用皮鞭抽他,他仍然不承认。但大家都认定他是个贼。一个晚上他偷偷地投河自杀,几天后尸体浮了起来,头颅肿得箩筐大。出了人命总归得有些说法,黄家从隔壁公社迁过来的,原来家族有位在县城工作的族人,便替他出头,将这个官司打到县里。最后那位生产队长判了三年徒刑,这个性格暴烈、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出狱后,变得脾气格外温和。社伢的弟弟是个脑子灵光的人,不爱干农活,整天东游西荡,也是光棍一条。
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后,社伢除了干自己那点农活很容易做完,他那年龄也不可能出去打工。于是便给短人手的家里收稻子、插田,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的成年子女多半打工去了。社伢一身力气,尤其当雇他的人像未庄人夸阿Q那样说:社伢真能做。他便更加卖力。
他喜欢来我家,一则因为我们兄弟在外面,父母喜欢别人来聊天;二则因为父亲从来不歧视他。母亲寿筵上,照样让他和别的客人一样坐席喝酒。他喝得高兴,喝完酒看别人打字牌,还在旁边替人出主意。打牌的人没谁理他,只顾自己玩自己的,大概觉得无趣,他抽着烟,哼着小曲,踉踉跄跄地往家走。
母亲对着他的背影说:人这样过,也是一世。
- 上一篇:怀念永远的外婆
- 下一篇:妈妈,你给了我生命的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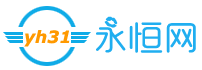

 会员登录
会员登录